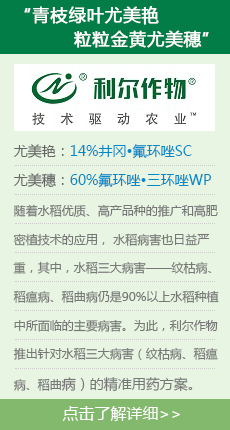原文作者:Christopher Preston, Patrick JTranel;编译:杨田甜
除草剂抗性机制一般分为靶标位点和非靶标位点两类。但是每一类中,还有不同的抗性机制。本文以澳大利亚杂草抗性为基础,综述了杂草抗性机制。
除草剂抗性机制一般分为靶标位点和非靶标位点两类。但是每一类中,还有不同的抗性机制。本文以澳大利亚杂草抗性为基础,综述了杂草抗性机制。
1 靶标位点抗性机制
靶标位点机制涉及与除草剂结合的蛋白发生变化,导致对杂草体内生化途径抑制的缺失。
最明显的是靶标蛋白内部发生突变,从而降低或消除了靶标蛋白与除草剂的结合。这是传统的靶标位点突变,并且是能对除草剂产生实际免疫力的典型。但并不总是如此,还有可能只发生弱的位点突变或强的位点突变。靶标位点突变可以是编码DNA的单点突变引起的,导致蛋白质上只改变一个氨基酸。这个被改变的氨基酸,可能会去除与除草剂相结合的键或者能改变结合袋(binding pocket)的形状。
靶标位点的突变,在A组、B组以及三嗪类C组除草剂的抗性中很常见,也在D组和M组除草剂中发生。(此处为澳大利亚除草剂分类,详见下文表格,后同)。由靶标位点突变导致的抗性容易在具有相同作用方式的除草剂中产生交互抗性。
对大多数靶标位点,都有可能产生多个导致除草剂抗性的突变。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的突变导致不同水平的抗性和不同的交互抗性模式。例如由磺酰脲类除草剂筛选的抗性不可能引起咪唑啉酮类除草剂的抗性。有研究表明,阔叶杂草对咪唑啉酮类除草剂发生交互抗性的机会是30%,而禾本科杂草是50%,但不同杂草种类之间有所区别。
ALS蛋白内部有8种不同的氨基酸,他们可能发生突变而引起对除草剂的抗性。其中4种可导致对磺酰脲类除草剂的强抗性,6种能引起对咪唑啉酮类除草剂的强抗性。因此,只有部分突变同时引起对磺酰脲和咪唑啉酮两类除草剂的抗性。 这是因为不同的除草剂与靶标位点的不同结合袋相结合,因此不同的突变只影响一种或两种类型除草剂的抗性。
A组除草剂有不同的情形。乙酰辅酶A羧化酶蛋白内部有7个氨基酸可以突变并对除草剂产生抗性。其中大多数是对苯氧丙酸类除草剂产生抗性,只有3个可以对烯草酮产生任何抗性,就其本身而言其中只有一种可以产生高水平抗性。因此,由苯氧丙酸类除草剂筛选的大多数靶标位点突变的杂草可以被烯草酮控制。在南澳大利亚种植者可以先用苯氧丙酸类除草剂防治黑麦草,当这些除草剂防治失败后再用烯草酮防治。一旦烯草酮也失去效果,则需要使用更高剂量,因为只剩下一个对烯草酮有高抗性的突变。
另一类靶标位点抗性是与正常情况相比,靶标位点基因的大量复制。在这种情形下,多出来的靶标位点像海绵一样吸收除草剂。这种抗性机制目前只在草甘膦抗性中出现。如果这种类型的抗性机制也出现在其他除草剂的靶标位点中,那么可以预料这种方式的抗性可以对任何除草剂起作用。详细内容见本文第3部分。
2 非-靶标位点抗性机制
非-靶位点抗性是指杂草阻止足够量的除草剂到达靶标位点,从而导致除草剂无法杀死它。杂草可能在开始时受到除草剂的影响,但是仍然可以存活并能产生种子。
最常见的这类抗性是因为对除草剂的解毒能力增强产生的。这种机制是除草剂在杂草体内被更迅速的降解从而使到达靶标位点的除草剂变少。杂草在开始时具有一定的除草剂解毒能力,后来在抗性杂草个体中这种解毒能力被大大增强。因此,增强代谢机制在A, B,C, D和I组除草剂中最为典型,他们都是选择性除草剂。
增强解毒抗性机制的实质还不清楚。但是,有证据显示是增强了几种酶的活性,而不仅仅是一种酶。这种抗性机制的一个后果就是导致不同作用方式除草剂之间频繁出现交互抗性,这就使抗性治理变得很复杂。交互抗性模式似乎高度可变而且难以预测,说明有多种类型的增强解毒机制。
除草剂解毒作用的一个变异体是降低除草剂的活性。有几种除草剂是以前体除草剂形式使用的,他们依赖植物的代谢功能将其代谢成有活性的除草剂。如果植物做不到这一点,前体除草剂就失去除草能力。这种抗性机制发生在加拿大的野麦畏(triallate)抗性上,在澳大利亚还没有发现。
第二种非靶位点抗性机制涉及除草剂在植物体内转运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除草剂被植物叶端收集,使得植物分生组织和其它部位的除草剂量降低。当需要除草剂到达生长组织才能杀死植物时,除草剂转运的降低就减少了到达这些关键组织的靶标位点的除草剂量。这种抗性机制在L组和M组除草剂中常见,但是在对A组除草剂抗性的杂草中也存在。
有几种抗性机制是通过降低除草剂的转运而产生的。主要机制似乎是通过将除草剂泵入细胞液泡中。由于涉及到除草剂的专一性转运子,因此往往只对一种除草剂产生抗性。一个例外是对百草枯的抗性杂草对敌草快也有交互抗性。
另一种降低转运情况是将除草剂困在从植物中脱落的组织中。这种“快速坏疽”抗性防效是植物对病原物攻击的响应机制,但是规模更大,整个叶片迅速死亡并脱落,将除草剂带走。这种抗性在其它地方抗草甘膦杂草种有发生(澳大利亚没有发现)。
其它两种非靶标位点抗性是理论上可能发生的,但是目前还没有抗性记录。杂草降低对除草剂的吸收可以降低到达靶标位点的除草剂浓度。这种机制只可能对那些仅通过叶片或主要通过叶片组织吸收的除草剂有效。另一种机制是植物有能力避免除草剂的有害作用,通常是通过增强处理氧自由基的能力。对百草枯的抗性机制被认为是这样的例子,而且只有当植物有能力快速地将除草剂从靶标位点移除时才成为有实际价值的机制。
3 除草剂抗性新机制--基因扩增
在除草剂抗性机制研究中,过去十年里最新奇的发现之一就是发现了基因扩增这种新的抗性机制。虽然基因扩增(包括编码解毒酶的基因以及编码靶标位点本身的基因)作为杀虫剂的抗性机制之一早些时候已经被证实,但是基因扩增作为除草剂的抗性机制直到2010年才见报道。在Gaines 等的这份报道表明在抗草甘膦长芒苋(Amaranthus palmeri)中编码5-烯醇式丙酮酸莽草酸-3-磷酸合成酶(EPSPS,即草甘膦作用靶标)的EPSPS基因被大量扩增(在某些植物体内扩增超过100倍)。但是后续的研究还没有阐明发生在长芒苋中的这种扩增的机制,尽管现在认为扩增的区域大的惊人(可能> 300 kb),并且除了EPSPS基因之外还包括多种基因。最近的一份研究报道,很多地理上分离的种群含有同样的扩增子,这表明这种扩增是一种罕见的事件,而且可能只在长芒苋中发生过。
EPSPS基因扩增已经在其他杂草的抗草甘膦生物型中发现,包括单子叶和阔叶杂草,如多年生黑麦草(Lolium perenne)、糙果苋(Amaranthus tuberculatus)和地肤(Kochia scoparia)。细胞遗传学分析揭示了物种间基因扩增模式的差异,尽管在长芒苋最初的报告中显示在整个基因组中似乎随机插入了大量的EPSPS,但在地肤和糙果苋中串联扩增占据EPSPS扩增的大多数或全部。不同的物种分布不同的EPSPS的扩增表明了多种扩增模式已经出现。
不管EPSPS扩增如何的升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对于其他的除草剂,基因扩增没有被观察到是一种抗性机制?”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杂草有“更容易”的进化解决方案,从而对其他大多数除草剂产生抗性。例如,乙酰乳酸合成酶(ALS)编码基因的任何一个单点突变,都会对抑制这种酶的除草剂产生很强的抗性。相比之下,已知的抗草甘膦突变位点则非常少,除了罕见的双突变,但他们造成的抗性水平比较低。因此,基因扩增可能是非常罕见的抗除草剂机制,只出现在很多常见的机制(靶标位点突变和增强除草剂解毒作用)不够的时候。
Laforest等的报道挑战了对这一问题的推理。他们报道马唐(Digitaria sanguinalis)以扩增编码乙酰辅酶A羧化酶(ACCase)的基因(大约5到8倍的拷贝)作为抗除草剂机制。就像对ALS抑制剂的抗性一样,有几个众所周知的靶标位点突变对ACCase抑制剂型除草剂有强烈的抗性。此外,增强对除草剂的代谢通常也作为一种抗ACCase抑制剂的有效抗性机制。因此,仅用缺乏其他可能的进化解决方案无法解释ACCase基因扩增作为一种抗性机制的演化过程。
关于ACCase扩增的细节仍有待阐明,包括拷贝是串联扩增还是多位点扩增。而且,虽然ACCase基因扩增与ACCase基因转录的增加有关,但还必须证明ACCase基因扩增和ACCase酶活性之间的关系,以证明基因扩增是否能充分解释抗性。事实上,尽管抗性高的马唐同型小种显示了对所有ACCase抑制剂的交互抗性,但对不同抗性级别的观察表明,额外的机制可能对同型小种的抗性也有贡献。尽管如此,现在似乎很清楚的是基因扩增是一种可能的抗除草剂的机制,而无需考虑具体的除草剂。
很有可能基因扩增并非是非常罕见的抗除草剂机制。有趣的是,Laforest等人在论文中指出,对于ACCase抑制剂的抗性机制有超过75%的已知案例都没有报道。类似地,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除草剂抗性案例没有报道其抗性机制。
Laforest等人的报告肯定会激发其他的研究者更多地研究基因扩增作为一种抗性机制,不考虑除草剂的作用方式。虽然目前已知的抗除草剂案例中由于基因扩增引起的除草剂抗性涉及靶标位点基因,但是非靶标位点的基因扩增正如已经被证实的作为杀虫剂抗性机制一样,几乎肯定也是除草剂抗性机制之一。
4 除草剂抗性是如何被筛选出来的
杂草的任何一种抗性机制都会因为除草剂的使用而被筛选出来。在实践中容易发生的是最强的抗性机制变成主导。最强的机制在除草剂筛选中具有更大的适应能力,因此携带这些机制的杂草个体会对种子库贡献更多。在大多数阔叶杂草中,对磺酰脲类除草剂的靶标位点抗性是最普遍存在的,因为它能对除草剂产生100倍的抗性。
在澳大利亚,不同作用方式的除草剂具有的主要抗性类型见表1。
表1 澳大利亚已经确定的不同作用方式的除草剂具有的抗性类型


表中各种作用方式字母的含义:
A= 乙酰辅酶A羧化酶(ACCase)抑制剂
B=乙酰乳酸合成酶(ALS) 或乙酰羟酸合成酶(AHAS)抑制剂
C=光系统II抑制剂
D=光系统 I抑制剂
E=原卟啉原氧化酶(PPG oxidase or Protox)抑制剂
F=类胡萝卜素生物合成抑制剂
G=莽草酸-3-磷酸烯醇式丙酮酸(EPSP)合成酶抑制剂
H=谷氨酰胺合成酶抑制剂
I=二氢叶酸合成酶抑制剂
K=有丝分裂抑制剂
L=纤维素抑制剂(Cellulose Inhibitors)
M=氧化磷酸化解偶联剂
N=脂肪酸和脂类合成抑制剂
O=合成生长素
P=生长素传导抑制剂(Auxin Transport Inhibitors)
Z=潜在的核酸抑制剂或非描述作用方式(Potential Nucleic Acid Inhibitors or Non-descript mode of action)
由于具有相同作用方式的除草剂品种之间抗性机制强度不同,因此不同的除草剂筛选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上世纪90年代,禾草灵(商品名Hoegrass®)是用于筛选野燕麦的主要除草剂。导致很多抗性种群对苯氧丙酸类除草剂都产生靶标位点抗性,而且对环己烯酮类除草剂也有一定抗性。后来精噁唑禾草灵(Wildcat®)和炔草酯(Topik®)成为最流行的野燕麦除草剂,也就出现了不同的抗性机制。这是一种非靶标抗性,因此导致对草氟胺(flamprop-methyl,即Mataven®)产生交互抗性。但是这些抗性种群对其它苯氧丙酸类除草剂仍属敏感。
不同的杂草种间仍然有不同的抗性模式。一年生黑麦草对B组除草剂的抗性绝大多数是靶标位点抗性,通常是因为这种机制能使其对氯磺隆(Glean®)和醚苯磺隆(Logran®)产生强抗性。但是在主要被碘磺隆(Atlantis®)和甲氧磺草胺(Crusader®)所筛选的雀麦草(brome grass),对绝大多数B组除草剂的抗性是低水平的非靶标位点抗性,同时对咪唑啉酮类除草剂具有很少或没有交互抗性。
对抗性杂草种群持续进行除草剂筛选会导致更强的抗性,通常是通过抗性机制的堆积产生。例如当一年生黑麦草对250mL/ha剂量的烯草酮(Select®)产生抗性后,发现绝大多数种群可以被500mL/ha剂量的烯草酮所控制。然后,又通过累积另外的抗性机制对更高用量的烯草酮产生抗性。当抗草甘膦的一年生黑麦草首次出现在葡萄园时,有些种植户增加草甘膦用量试图控制黑麦草。他们对黑麦草所筛选的结果是两种不同的抗性机制,靶标位点突变和降低除草剂转运,导致对草甘膦抗性更强。
杂草也能通过积累抗性机制对多种作用方式产生抗性。这种情况通常是经过相继地使用不同作用方式的除草剂产生的,但是也可以通过除草剂轮换使用或者使用除草剂混剂而产生。多重抗性最易在异型杂交杂草中产生,也容易在自花授粉的杂草种群中产生。最糟糕的多重抗性是黑麦草种群对A、B、C、L 和M组除草剂的多抗性。这个抗性种群同时具有靶标位点抗性和非靶标位点抗性机制。
5 除草剂测试的作用
虽然可以通过特定除草剂筛选的方法对大多数常见的抗性机制做出一般性预测, 但是抗性机制的多样性和除草剂使用历史的多变说明在任何单个种群进行抗性机制的预测是困难的。除草剂测试之所以有用,不是因为能确定抗性种群是否存在,而是能确认出仍然有效的除草剂。一块地里的某个种群对替代除草剂的反应与邻近地块里的另一个种群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不同的混合抗性机制的筛选。因此,在一块地里的某个种群所做的测试结果不能对邻近地块将要发生什么做出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