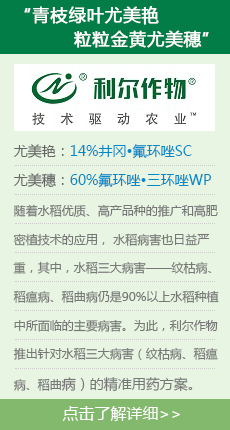“原本人们没有农药就没饭吃,所以需要农药;现在有饭吃了,我们开始考虑它的残留、风险、环境污染等,这是对的。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人们对农药的需求。”中化国际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刘长令,在日前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人们谈“药”色变,实际上是对农药有较深的偏见。
刘长令1963年生于河南,曾任沈阳化工研究院总工程师,现任中化国际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兼任中国化工学会农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农药(沈阳)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2014年,其研究团队创建了绿色农药分子设计和品种创制的“中间体衍生化法”,发表在化学领域顶级期刊《化学评论》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化国际,600500)脱胎于中国中化集团的橡胶、塑料、化工品和储运业务,于1998年12月在北京成立。2000年3月,中化国际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农药,指农业上用于防治病虫草害及调节植物生长的化学药剂,按品种分包括杀虫剂、杀螨剂、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
公众谈“药”色变,缘起甲拌磷等高毒性农药
刘长令认为,公众谈“药”色变,很大程度上是受以前一些高毒农药引发的事件影响。刚开始中国生产的农药品种主要是高毒的有机磷类杀虫剂,因此人们将杀虫剂与农药等同起来,但实际上这类真正令人谈之色变的“农药”已经被淘汰许久。
以前中国生产的许多杀虫剂属于有机磷类,如常用的对硫磷(1605)、甲拌磷( 3911)、内吸磷(1059)、敌敌畏等。这些常用的有机磷农药中,根据大鼠急性经口半数致死量(LD50,数值越小毒性越大),有LD50量在4 mg/kg ~10 mg/kg的内吸磷,2.1 mg/kg~3.7 mg/kg的甲拌磷等高毒性农药。
根据农业生产上常用农药(原药)的毒性,按照急性口服LD50数值,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和微毒五类。据统计,目前中国批准使用的农药,94%都属于低毒和微毒级别, 5%属于中等毒。
2002年原农业部发布公告,禁止内吸磷(1059)、甲拌磷(3911)等高毒农药在蔬菜、果树、茶叶和中草药材上使用。
刘长令提到,曾经还有一种令人色变的农药则是滴滴涕(DDT)。在农药的历史上,DDT 是第一个被人工合成的广谱而高效的有机氯杀虫剂。1939 年瑞士化学家首先发现 DDT 可以作为杀虫剂使用,并于1948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自此,以 DDT 为首的有机农药成为粮食增产的重要手段,彼时每年减少的作物损失约占世界粮食总量的 1/3。
上世纪70年代左右,中国引入滴滴涕。在全球使用几十年后,人们发现滴滴涕类农药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用药6个月后的农田里,仍可检测到滴滴涕的蒸发。此外滴滴涕极易在人体和动物体的脂肪中蓄积。
中国在1982年禁用了滴滴涕,但是仍然将其用于应急病媒防治、三氯杀螨醇生产和防污漆生产。2009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公告,要求禁止在中国境内生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滴滴涕,但保留了紧急情况下用于病媒防治的可能。
滴滴涕类农药的毒性来自于富集而产生的毒性,也就是说如果有残留,由于人体不能靠代谢排出去,体内的滴滴涕就会富集,从而产生高毒性。刘长令介绍,现在的农药在上市前,如果检测出有蓄积毒性,即停止开发,不会被批准上市。
“我们永远都无法说农药没毒,永远不能否认农药有残留。”刘长令表示,化学品毒性和残留问题,都需要得到正确的认识,是否产生危害都与量有关,“那氯化钠的大鼠急性经口LD50差不多是3750mg/kg,氯化钠就是食盐,每天食用超过20克,长期下来就会对身体有害。事实上,现在使用的农药中没有富集性,且一部分农药的大鼠急性经口毒性低于食盐,在食物中的残留量也远低于0.05mg/kg。”
此外,农药的残留问题还与使用的规范化有关。刘长令向记者介绍,假如一种农药一亩地只需要用1克,在做实验阶段就会用100克去做。在“极端施药”的情况下,测量并规定最大残留限量(在食品或农产品内部或表面法定允许的农药最大浓度,mg/kg)、每日允许摄入量(人类终生每日摄入某物质,而不产生可检测到的危害健康估计量,mg/kg bw)等残留限量标准。
其次,施药有安全间隔期,就像有时候人吃完药以后要过30分钟才能吃其他东西。农药也是一样,用完某种药以后,一般会规定过多少天之后才适合采收。
因此刘长令认为,如果没有“疯狂用药”或“着急采收”,并不会存在农作物药物残留导致人类的健康问题。
农药仍是治理农作物病虫草害的首选
“现在60岁左右的人,都经历过没有饭吃的日子,我们小的时候根本没有农药,但作物收成也非常非常低。”刘长令表示,完全不施药情况下的粮食亩产,在以前尚无法让所有人吃饱,更不要说解决现在14亿人口的温饱。
而如今,人口依然在增长,随着工业化发展,耕地面积相对来说还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提高农作物单产来保障人们的口粮。
刘长令提到,提高单产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种子、土壤管理、各种作物保护措施等等,实际上都在使用,但效果并非立竿见影,尤其是在防治病虫草害方面,农药仍然是首选。
刘长令介绍,40年前曾经历过的一件事,小麦田爆发一次虫灾,当时没有农药,组织了数百学生去抓虫子。“这么多人进地里灭虫,虫是灭光了,庄稼也破坏得差不多了,收成也没有了。”
此外,包括黄瓜霜霉病、马铃薯晚疫病等农作物病害可以通过气体传播,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黄瓜叶子或马铃薯叶子得了病,人一经过或者刮过风,整个大棚都会爆发疾病。“农作物和人一样,不生病的时候要保持良好的营养、预防疾病,但生病了就要吃药。”
此前澎湃新闻采访的多位科学家也表示,粮食增产的办法除了生物技术,就是化学农药。刘长令认为,生物技术是让农作物抗病虫害的办法之一,但作物一个生长季可以受到数种或几十种病虫害的危害,目前的生物技术尚未能实现让一种农作物抵御所有病虫害,因此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需要结合使用。
据刘长令介绍,世界粮农组织(FAO)有一项统计表明,通过合理地使用农药,作物产量的损失可以减少40%,同时也可以减少作物本身抵御病虫害而产生的毒素,利于人畜健康。
此外,刘长令还提到农药市场的反应。2018年受环保治理的影响,部分农药的生产受到限制,价格不断上涨。原本一吨价位在30万左右的杀菌剂氟环唑,在2018年8月时价格飙升至68万元/吨。
“这就简单地说明一个问题,农药的需求是刚性的,少了价格就会上涨。”
农药的创制与医药相似:研发时间长、成功率低
与医药相似,国内的农药也是从仿制药开始。刘长令表示,在目前常用的六七百种农药中,大约有98%左右的农药均为仿制药,国内拥有自主专利权的农药少之又少。农药和医药都存在着研发周期长、成功率低从而导致风险大、投入高的问题。刘长令认为,和医药相比,农药对成本的要求更加严格。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没有人到医院会说,你这个药太贵了,我不用。你肯定认为哪个药好用就用,贵就贵点。”刘长令说,“但是农药不一样,太贵就不会有市场,大不了种地的人这次就选择少收成。”
以前由于普遍的检测技术较为落后,三五年一款农药就能研究或仿制出来,随后上市,包括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并未得到充分认识。
随着技术越来越先进,人们具备了更多种毒理学测试和环境评价的能力,对农药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刘长令介绍,1956年左右从800个化合物中就能筛选出一个产品,到了1970年需要8000个化合物筛选一个产品,1980年后大约2万个化合物才能筛选一个产品,现在基本上16万个化合物才能筛选出一个产品。
以一个30人组成的团队来合成16万个化合物,每人每年约合成150个,则差不多需要35年时间。这就使得农药创制的周期变得很长。刘长令表示,目前号称一个产品研发需要12年,实际指的就是开发阶段,并未包括前期研究阶段。
除了周期长以外,成功率低也是一大“劝退因素”。在寻找化合物的阶段,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化合物具有很好的活性,可以优化、衍生或修饰;在功能上合适的话,接下来要进行各种毒性测试、残留和代谢研究与检测,生态环境风险评估等,包括低毒、低残留、有无致癌性、无突变型,对蜂鸟鱼蚕、土壤和水等生态环境等有多大影响,这一研究过程需要6到8年,大多候选品种在这一“大浪淘沙”的过程中被淘汰。进入工业化生产阶段后,则需要研究合成工艺,性价比不好的候选品种依然被淘汰,随后进行小试、中试,再到产业化大规模生产。与医药一样,每一步测试的淘汰率都非常高,也就意味着成功率低。
上世纪80年代,刘长令发现部分农药虽然品种不一样,但其使用的原料或中间体一样,随后刘长令在25年间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并创建了“中间体衍生化法”。
1997年,刘长令团队发表了《浅谈中间体的共用性》论文; 2014年受邀在化学领域顶级期刊《化学评论》发表综述论文“中间体衍生化法在新农药创制中的应用”。2017年,《化学评论》的影响因子为52.613,在化学化工领域期刊中排名第一,在全球期刊影响因子排名中超过《自然》和《科学》。
刘长令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中间体衍生化法是基于逆合成分析和现实生产的可行性基础创建的。比如观察一个房子,各种类型的房子可能长相用途不一,但往前推,观察其框架、设计和原料,最后发现原来就是沙子、水泥、钢筋、砖头等几种原料。
农药也是一样,大多数农药都是由最开始的几个原料组成的,通过各种不同的反应,最后得到不同的产品。选对了中间体就选对了原料,选对了安全且价廉原料来做反应,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半,提升了研制低毒、安全、性价比高候选品种的几率,也就提高了研发的成功率。
天然产物是实现农药绿色化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刘长令团队以天然产物为模板和中间体,发明了肉桂酸衍生物类杀菌剂氟吗啉,成为国内第一个在中国、美国和欧洲获得专利权的农药品种。此后又发明了仅含碳氢氧三种元素、可用于苹果树腐烂病等防治的杀菌剂丁香菌酯,和具有杀菌、抗病毒、促进作物生长调节活性的唑菌酯,并制定了唑菌酯原药及制剂两项国际标准。
农药的未来:低量高效,环境相容
对于未来的研究方向,刘长令认为,农药和医药一样,始终不变的课题就是新产生的病虫草害及抗性管理。受气候环境的影响,新的病虫草害时有发生,而任何药物,长期使用就会产生抗性。刘长令表示,新产生的病虫草害及抗性管理,都需要不断开发新产品;而农药的棘手问题就是防治对象变异快。
对医药而言,目前人类约每20-30年繁衍一代,高等生物产生抗性的机理虽然复杂但每一代变化不大。而农药面对的是低等生物,繁衍速度快,变异也快,比如螨虫在纬度较高的地方一年可以繁衍30多代,而哪些变化会影响病虫草害产生抗性,将是农药研究亟待攻克的问题。
就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就是要考虑环境相容性,刘长令表示,现在的检测技术已经完全可以达到微克级(ppm,溶质质量占全部溶液质量的百万分比来表示的浓度),有些甚至纳克级(ppb,溶质质量占全部溶液质量的十亿分比来表示的浓度)。如果在纳克级检测出来有明显问题,也会在研究过程中被淘汰。
但另一方面,也存在某一款药物可能对某一种生物有害,但经生态环境风险评估依然被批准销售。这则是因为在尚未出现更好替代品的情况下,若对当下对环境的潜在影响风险较小,就选择保留。刘长令向记者举了个例子,比如某种小麦除草剂,可能对鱼的毒性较高,但这种小麦田离有鱼的地方比较远,在安全评估后认为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对鱼的影响小到一定阈值以下,也会批准上市。
“做任何事情是一个平衡,农药不用不行,但用了就希望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尽可能低。”刘长令表示。
2015年,原农业部下发《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2017年年底,原农业部表示,已提前三年实现农药零增长的目标。
作为农药创制人员,刘长令认为,所谓“零增长”,其实只是在使用量上进行了限制,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保证产量的情况下,实现农药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并不困难。
“如目前在产业化开发中的除草剂,测算下来一亩地最多只需要用4克,而草甘膦一亩地差不多要使用100克,如果成功上市并实现对草甘膦的替代,使用量大幅减少不成问题。”
所以在刘长令看来,对农药的使用规制,并不仅仅是使用量零增长,而是通过对生态和环境毒性愈加全面的检测,将不合规的老产品淘汰。未来高效又安全环保的绿色农药将大有作为,尤其非常需要环境相容的绿色农药品种。
“零增长是第一步,之后是安全环保低风险,虽然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零风险的,但效果好、环境相容、零风险、绿色农药的创制与应用是终极目标,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刘长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