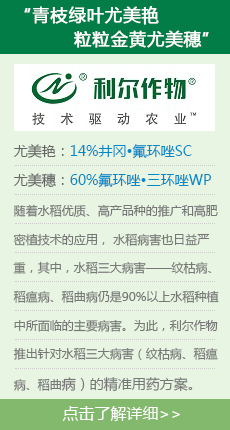植物源提取物通常是指以植物为原料,通过清洗、过滤、提取、分离、浓缩、萃取、精制等物理手段,有效清除植物中的杂质等成分,不改变其原有化学结构而最终获得的一种或多种有效成分。以不同目的而获取的植物提取物的终端产品可作为生物活性物质、食品添加剂和香料等,被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及植物源农药等各个领域。
我国对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神农氏,在《周礼》《山海经》等先秦古籍,以及后来的《神农本草经》《齐民要术》《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历朝历代的中医、农事著作中均有使用植物性物质防治农业有害生物的记载。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人们对植物原材料只是经验性的利用。加工利用方法也只是简单的干燥研磨或焚烧熏蒸,并没有对其有效成分作深入探究和利用。
1 主要植物源农药品种的商品化
第一个商业化植物源杀虫剂出现在17世纪,烟草中的尼古丁被发现并开发上市,用以防治豆象虫。19世纪上半叶除虫菊素和鱼藤酮也先后从经验利用迈入研究应用阶段,并商品化。很早人们就利用精细研磨的除虫菊花粉来防治虱子和跳蚤等寄生虫。除虫菊素的主要成分为天然除虫菊酯,是从除虫菊植株中提取的有机酸和醇酮形成的酯类化合物,其中含量最高的除虫菊素Ⅰ和Ⅱ是主要的杀虫活性成分。1828年,除虫菊酯类农药首先在美国上市。
1848年,Oxley最先报道了从毛鱼藤(Paraderris elliptica (Wall.) Adema)的根部提取出杀虫活性物质鱼藤酮,自此鱼藤酮作为杀虫、杀螨剂和鱼毒剂开始在亚洲和南美洲使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们分离纯化得到鱼藤酮化合物,并确定其分子式和结构式。
上述植物源杀虫剂一直沿用至今。二战后高效化学农药蓬勃发展,一跃成为控制农业害虫的主要手段。植物源杀虫剂的应用与研发一度陷入低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化学农药的弊端逐渐暴露。化学农药滥用所造成的生态问题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农药这把“双刃剑”。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有机合成农药的“3R”问题凸显,农药残留(Residue)、害虫的再猖獗(Resurgence)与抗性(Resistance)问题促使人们着手发掘环境友好型农药。于是人们重又把目光投向古老的植物源领域。
植物源农药的有效成分多为植物在进化中产生具有保护作用的次生代谢物质,这些物质往往可以抵抗其他生物的侵害。自然界中具有杀虫或杀菌活性的植物次生代谢产物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如萜烯类、生物碱、类黄酮、甾体、独特的氨基酸和多糖等。而这些物质对非靶标生物毒性较低,并且易降解,不会对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持久性影响,安全性较高。
随着对植物源活性成分研究的深入以及超声波萃取法、微波萃取法、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等新提取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植物源农药得以商品化。
20世纪60年代,印楝素迎来了它的发展机遇。印楝素是从印楝(Azadirachta indica Adr. Juss.)中提取的一种植物源农药,现已经成为植物源杀虫剂的代表,具有作为理想农药的众多优点:广谱、对天敌干扰少、无明显的脊椎动物毒性或植物药害、环境中迅速降解、地区性资源丰富、可再生。德国、美国、印度等国先后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研究印楝的杀虫活性物质,掀起了国际性研究热潮。Butterworth和Morgan于1968年成功地分离印楝素(azadirachtin)。Broughton等确定了印楝素的主体化学结构。1985年以印楝素为主要成分的第一个商品药剂Margosan-O在美国获准登记。这是继除虫菊后第二个被批准在美国使用的植物源农药。
联合国在一份报告中称印楝是“本世纪对当地居民的最大恩赐”,印楝被美国农业部誉为“可解决全球问题的树”。印楝杀虫剂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生物农药之一,其国际影响与市场空间日益扩大。我国于1997年批准印楝素的临时登记,2009年6月,成都绿金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10%印楝素母药和0.3%乳油成为国内首次取得正式登记的商品化印楝素产品。
我国的传统中药不仅为现代医药学的宝库,同样也为植物源农药的筛选研发提供丰富的资源。我国登记的源于中药的植物源农药不在少数,如苦参碱、蛇床子素、雷公藤甲素等,其中也不乏成功产业化利用的优秀药剂。
苦参碱(matrine)是豆科植物苦参(Sophora flavescens Ait.)、苦豆子(S. alopecuroides L.)、越南槐(S. tonkinensis Gagnep.)等中草药的活性成分。苦参碱属于四环喹嗪啶类化合物,分子骨架可看作2个喹嗪啶环的稠合体。近年来,发现苦参碱具有抗心律失常、抗炎、抗纤维化、抗肿瘤等多方面重要的药理活性,各类制剂已被广泛用于临床。苦参碱在农业上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目前作为农药登记用于防治的害虫有大螟、甜菜夜蛾、韭蛆、小菜蛾、茶尺蠖、茶毛虫、茶小绿叶蝉、蚜虫、烟青虫、小地老虎、蓟马、叶螨、美国白蛾和松毛虫14种,病害有梨树黑星病、黄瓜灰霉病、烟草病毒病、葡萄灰霉病、葡萄炭疽病、黄瓜霜霉病、番茄灰霉病、马铃薯晚疫病和水稻条纹叶枯病9种。
相较于其他植物源农药,苦参碱具有更高的安全性。陈昂参照《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中农药对非靶标生物的安全性评价方法,分别测试了印楝素、除虫菊素、鱼藤酮、苦参碱、蛇床子素5种植物源农药对蜜蜂、鹌鹑、斑马鱼和家蚕的急性毒性。结果表明,印楝素、除虫菊素和鱼藤酮对非靶标生物的毒性较高,尤其对家蚕风险性大;苦参碱和蛇床子素毒性很低,相对安全。
蛇床子素是从传统中药中提取出来的又一天然植物源化合物,一直被广泛应用于医药,其与苦参碱一样具有杀虫抑菌的双重作用,尤其对作物白粉病防效显著。该化合物作为农药应用为中国首创,2003年首次获得国家专利并获得农药临时登记上市销售。
2 我国植物源农药的应用现状
2.1 我国植物源农药的登记情况
根据2017年FAO和WHO联合发布的《用于保护植物和公共卫生的生物农药登记指南》(Guidelines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microbial, botanical and semiochemical pest control agents for plant protection and public health uses)的规定:植物源活性物质(Botanical active substance)是由植物中一种或多种成分组成,通过将同种植物的全部或多个部位进行压榨、碾磨、粉碎、蒸馏和/或提取等过程而获得。该方法也可包括进一步的浓缩、纯化和/或混合,但不应通过化学和/或微生物过程有意修饰或改变各组分的化学性质。
2017年新《农药登记资料要求》发布,提高了登记门槛,对植物源农药登记管理更加科学规范。
截至2019年底,我国在登记有效期内的植物源农药有苦参碱、鱼藤酮、印楝素、藜芦碱、除虫菊素、烟碱、苦皮藤素、桉油精、樟脑、右旋樟脑、八角茴香油、狼毒素、雷公藤甲素、莪术醇、蛇床子素、丁子香酚、大黄素甲醚、香芹酚、小檗碱、甾烯醇、茶皂素、螺威、苦豆子生物碱、大蒜素、d-柠檬烯、萜烯醇、异硫氰酸烯丙酯、银杏果提取物(十五烯苯酚酸、十三烷苯酚酸)、补骨脂种子提取物(苯丙烯菌酮)共计28种,登记单剂数量总共247个,混剂36个,母药/原药41个,登记企业177家。
我国登记的植物源农药单剂主要集中在苦参碱、除虫菊素、印楝素、蛇床子素、鱼藤酮以及卫生杀虫剂樟脑六大品种。以上每个品种相关登记企业都在15家以上,其中苦参碱的登记企业多达94家,占所有植物源农药登记企业的53%(表1)。苦参碱单剂的登记数量占农用植物源农药品种登记单剂数量的45%(图1)。
表1 我国植物源农药登记情况




图1 我国登记农用植物源农药单剂种类组成
除以上六大主要品种外,丁子香酚、小檗碱、藜芦碱、苦皮藤素、香芹酚以及传统烟碱的登记企业有5~10家。登记作物和病虫害也相对比较丰富。剩余品种制剂单一,登记企业有1~2家,但大多独具特色,针对性强。如莪术醇和雷公藤甲素都是比较成功的植物源杀鼠剂;甾烯醇主要登记用于防治病毒病;大蒜素登记防治细菌病害等。
据有关部门统计,2012年我国植物源农药年产量突破千吨大关的有苦参碱(5,858 t)、印楝素(1,554 t)和狼毒素(1,170 t);雷公甲藤素(600 t)、除虫菊素(376 t)、八角茴香油(354.5 t)、鱼藤酮(287 t)、蛇床子素(271 t)、丁子香酚(225 t)和樟脑(200 t)也都在200 t以上。调查中处于正常生产的植物源农药品种只有14个,有不少尚在登记状态的品种并未生产。
尽管前期筛选出多种具开发价值的农药活性植物资源,但由于受到植物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以及受国民经济现状和使用者认知水平的影响,目前产业化的植物源农药品种仍然较少。有不少已成功进入登记应用阶段的品种如羊角扭苷、辣椒碱、楝素、百部碱、莨菪碱、乌头碱、马钱子碱等,由于市场等多方面原因,而在登记到期后未能延续。
2.2 植物源农药存在的应用误区
植物源农药因其环境友好性而受到人们的青睐,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人们往往只关注有效成分的天然属性。“植物源”并不等同于环境友好,植物源农药的提取加工过程同样要涉及众多物理化学工艺,如压榨、研磨、蒸馏、提纯以及剂型加工等。
从农药先导化合物的研发层面来讲,广义的“植物源”不单指物质本身,更包含其背后可被研究开发利用的作用机理等。为提高杀虫效果、提高有效成分化学稳定性、解决抗药性及产量等问题,在植物源农药基础上经化学修饰和人工化学合成发展起来的新烟碱类和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植物源农药”。如新烟碱类杀虫剂虽然源自对天然生物碱的结构优化,但无论从理化性质、杀虫性能还是生产过程来看都已经是化学合成农药。无论是合成生产环节的工业“三废”,还是使用环节对非靶标生物及环境的负面影响都与植物源农药的绿色初衷相去甚远。由于新烟碱类农药对蜜蜂的毒性,噻虫胺、吡虫啉和噻虫嗪在欧盟已被禁用,我国也启动了对这类农药的再评价。
传统的卫生用杀虫剂樟脑,其自然成分是从樟树树干中提取,一度导致对樟树的过度砍伐。台湾自古盛产樟脑,在19世纪年产量约占全世界总产量的70%~80%。1868年英国侵略者为掠夺台湾的樟脑资源,逼迫清政府签订《樟脑条约》。日占时期日本政府更是对我国台湾北部原始樟树林加紧砍伐与掠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台湾樟脑输出量长居世界首位。而一味依赖砍伐难免竭泽而渔,对当地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如今,天然来源的樟脑由于资源匮乏及保护等原因已经远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樟脑市场需求。目前,市场上的樟脑以松节油为原料生产的合成樟脑为主。合成樟脑虽然在化学结构上与天然樟脑并无二致,但其“植物源”的身份早就名不副实。
这些广义的“植物源”农药不能简单与环境友好划等号。在美国,许多植物源农药仍作为传统农药 (conventional pesticides)而未列入生物农药(biopesticides)管理。2017年,FAO和WHO联合发布的《用于植物保护和公共卫生的微生物、植物源和化学信息素类的生物农药登记指南》也将经化学和/或微生物过程有意修饰或改变各组分化学性质的物质排除在植物源活性物质之外。
随着新《农药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国家对农药的管控日趋科学、细致、严格。管理措施贯穿农药的研发、登记、生产、经营、使用及废弃物回收全过程。《农药登记资料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569号)规定农药制剂登记需提供详实的加工方法描述资料。登记植物源农药制剂同样需提供生产工艺描述资料,包括原材料、生产工艺说明、生产工艺流程图、生产装置工艺流程图及描述、生产过程中质量控制措施描述。
这些举措表明,农药管理者不只关注农药制剂本身的毒性和安全性,同样也关注农药生产加工过程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植物源农药是否具有环境友好性,需将生产加工过程一并纳入考量范围。
人类的工业生产活动是主要的污染物来源。除了农药产品以外,农药生产加工过程中的中间体、附带产品等随“三废”直接排放到环境中。这部分污染源属于工业生产过程产生,通常由工业环保部门管控。随着农药监管向生产延伸,通过农药登记对农药入市实施把控,能有效引导农药的研发及生产工艺向环境友好型转变。
另外,植物源也不等同于安全。除了原料获取和制剂加工过程的生态和环境风险以外,植物源农药本身的安全性实际上也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我国新近开发的植物源杀鼠剂雷公藤甲素,其植物源性也被作为该药物安全性宣传的重点之一。但从雷公藤甲素毒性作用时间以及毒力来看,该药实际上属于急性杀鼠剂。而杀鼠灵是从香草木樨(属)的青贮饲料中发现并提纯应用的化学制剂,也是植物源产品,并且是目前毒力最低的抗凝血类杀鼠剂之一,但仍被收录入我国危险化学药品名录,并未见任何国家从其植物源属性宣传其安全性。
3 植物源农药产业发展建议
农药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药剂更新换代日新月异。植物源农药的研发机制不像化学农药那样完善,研发和产业化都较为困难。同时,植物源农药产业的发展仍需考虑市场规律。植物源农药的生产受原材料的限制。科研中发现的许多适宜制取植物源农药的植物难以种植,商品化过程中难以获得充足的高品质材料用以分离活性物质。另外,活性物质分离提取工艺和生产企业技术装备也是限制植物源农药产业化的一大因素。但植物源农药环境相容性高,其低毒、无残留的优点正越来越受到广大农业从业者的青睐。其在有机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等高质量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应用潜力巨大,市场前景广阔。植物源农药产业方兴未艾。
3.1 坚持以绿色为导向
植物源农药鲜有防效能够超越化学合成农药的制剂。相较于化学农药,植物源农药的优势在于概念上的生态安全,能够满足民众健康环保的需求。这是植物源农药能够存续和发展的根本。植物源农药不必追求最高的防治效果,以能达到经济损失阈值以下为目标即可作为优异的防治备选药剂。
国家农业部于2015年2月下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大力推进化肥减量提效和农药减量控害。我国开始对农药使用量进行宏观调控,探索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植物源农药坚持以绿色为导向,顺应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和国内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3.2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品种
植物源农药制剂的研发和生产受原材料的制约,在与高效、廉价的化学农药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能否因地制宜地依托当地容易获得的原材料开发新品种,是植物源农药产业能否长久存续并发展的关键。
植物源农药严重依赖植物资源。从19世纪我国台湾兴起的樟脑产业,到20世纪末印度兴起的印楝素产业,再到占据我国植物源农药半壁江山的苦参碱,成功的产业化推广应用的植物源农药除了有效成分本身的特性和可操作的提取工艺之外,原材料是否稳定来源渠道也是必要条件之一。原材料的获取有野生采集和农业种植两种方式。农业种植需要培育,在产业化初期尚可依靠农民野生采集、企业集中收购的方式发展。随着产业的发展,需因地制宜地扩大种植以保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如我国云南地区的印楝种植、广西地区鱼藤的引种以及北方苦参的种植,都是植物源农药产业能够立足并发展的根本。在原材料的供应模式中以印楝素为代表的种子收获及提取加工模式最为环保:一方面印楝为多年生速生落叶乔木,种植无需像除虫菊及苦参等一样占用耕地;另一方面只需收获种子以供加工提取,无需砍伐植株,比起樟脑等的植株提取模式,能更好地保护当地生态植被。这也是印楝素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另外,根据地区植物资源开发特色植物源农药品种也是产业能够成功的途径。如徐州市金地农化有限公司背靠江苏省邳州市和山东省郯城县两处中国最具盛名的“银杏之乡”,开发登记的银杏果提取物就是成功的案例。此外,还有西北地区的狼毒素(甘肃国力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及内蒙地区的苦豆子生物碱(鄂尔多斯市金驼药业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登记已到期)等产品。
3.3 登记作物和防治对象适当向经济作物倾斜,打造精品农药
人们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国家对农药管控力度不断加大,特别“三品一标”高品质农产品生产对农药要求更为严格。产品附加值高使得成本较高的植物源农药更易被市场接受。从目前登记情况来看,植物源农药大多登记在蔬菜、茶叶、草莓及果树等经济作物上。这符合植物源农药绿色环保的特点。但目前的登记作物和病虫尚难以满足生产需要,发展空间很大。
以葡萄为例,我国葡萄虫害多达130多种,分布普遍、危害较重的就有近10种。而截至2019年底,我国登记的葡萄用杀虫剂仅有4个品种(防治盲蝽蟓的氟啶虫胺腈,防治蚜虫的苦参碱,防治绿盲蝽的苦皮藤素和防治蚧壳虫的噻虫嗪),可谓杯水车薪。而截至2016年底,我国葡萄栽培总面积为80.96万hm2,仅次于西班牙,居世界第二位;产量达1,374.5万t,居世界第一。其中,我国葡萄产量80%左右为鲜食葡萄。东南沿海发达省份部分地区葡萄每667m2产值早已超过万元大关,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几年上海地区鲜食葡萄平均每667 m2的产值甚至超过1.6万元。而“三品一标”等高质量的精品葡萄产值更高。高产值使得农户在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上的投入可以说是“不计成本”。
随着农药残留监督抽查和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的完善,对“非法”用药现象的查处力度将会加大。经济作物农药产品登记的空白将会显现,生产中对绿色精品农药的需求将给植物源农药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 小结
植物源农药的兴起源于人们对“寂静的春天”的深刻反思,承载人类对绿色农业的美好愿景。2015年,在菊科蒿属植物黄花蒿(Artemisia annua L.)中发现青蒿素的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随着科技和理念的进步,植物源领域越来越多的成果涌现。植物源农药天地广阔,如何用好自然的恩赐将继续考验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药管理者的智慧。
作者:张正炜1,郗厚诚2,常文程1,黄璐璐1,陈秀1,3(1.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2.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3.上海市农药检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