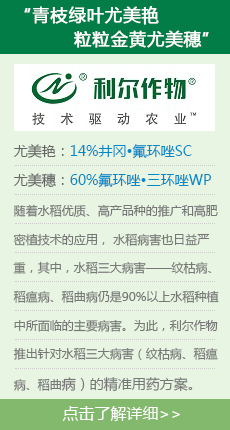追溯植保新分子的发展历程,那些现代有机合成的早期产物如DDT和卤代烃之类就可满足植保要求,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一些较易发现和合成的化合物逐渐早已被开发出来,发现和合成一个新分子变得愈发困难。雪上加霜的是,大大增大的研发投资的成本,一个产品从研发到面市的花费在2000年为1.84亿美元,而到了2008年,这个费用上升到了2.56亿美元,更艰难的是,往往从14万个待选化合物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新分子,而且还要经过上百次效力和安全性检测才能最终投入市场。此外转基因作物开始盛行以来,人们对化学控虫产品的需求锐减,而种子性状产品开始盛行其道,在过去的五年内,这类产品的销售额上升了16.6%。
好在一些顶尖的农化公司,如先正达,拜耳,巴斯夫,杜邦和陶氏仍旧为研发植保新分子乐此不疲地投入着数千万美元以保证自己的研发能力,它们也的确可以研发出能够轰动一时的产品,如除草剂,杀虫剂,杀菌剂等,只是数量远远不不及以前而已。
除草剂:缺乏新机制下寻找“抗性”市场
史上也没有什么其它因素能像转基因作物这样影响到除草剂产品的发展, 因为有了除草剂,再也用不着锄头来人工除草的新方式的确大大改变了种植业,但是耐除草剂转基因技术推广给种植业的影响则更迅速,对于那些销售非草甘膦的公司来说,和草甘膦产品的竞争无疑是一个噩梦!然而草甘膦的好景并不长,经过十多年的大量使用之后,这个产品因为抗性杂草的出现而风光不再。那些往日视草甘膦为救命稻草的不得不使用具备不同除草机理的产品来应对草害抗性问题。
虽然科学家共发现了22个除草剂作用机制,但是近来20年却未开发出任何一个新机制,这导致了杂草对很多常见的除草剂产生了抗性,苋菜藤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对五种不同类型的除草剂均产生了抗性,并且在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和大豆田中肆虐,而人们却拿它似乎无能为力。
因此一些公司也因此开始从草害抗性上寻找商机,去年在美国成功亮相的除草剂Kixor,使巴斯夫公司成功地在这个领域挖到第一桶金。很多公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断了除草剂的研究,巴斯夫公司虽然研发上起步稍晚,但因为坚持了下来,最终得到了回报Kixor属于苯并异噻唑类除草剂,通过抑制前原卟啉IX氧化酶来影响阔叶草类的叶绿素合成,这类产品的作用机制其实并不新颖,早先已经有类似产品得到过应用。巴斯夫公司作出的改动是对苯并异噻唑上的一个侧链进行修饰,使得产品对草类叶面有了更强的粘附能力,增强侧链的亲脂性使得它能更好地和目标连接。Kixor可以良好地控制阔叶草类,还能控除部分其它草类,然而它最大的价值在于能控除那些对草甘膦产生抗性的杂草。它在种植前使用,这个步骤通常叫做“烧毁”,而农民们早已经习惯于在开始生长的作物上使用草甘膦了,这种方式可以杀灭隐藏在庄稼行间的杂草,巴斯夫的研发线上同样有着相关的转基因作物,如对一些老旧产品,如麦草畏,咪唑啉酮类产品具备抗性的性状产品。
陶氏同样也想在“抗性”市场上分一杯羹,它把目标投在了一个老旧产品——2,4-D上,开始进行相关性状转基因产品的开发。先正达和拜耳作物科学也开始进行了耐硝草酮大豆以及其它耐羟苯基丙酮酸双氧化酶HPPD抑制剂转基因作物的开发。
除了以上进展,包括先正达,拜耳,巴斯夫,杜邦和陶氏在内的几大巨头所公开的研发计划中,除草剂产品寥寥无几,陶氏只有两个除草剂处于开发中,先正达也只有另一个HPPD型产品bicyclopyrone处于研发中,据称能控除玉米和甜菜中的阔叶草和牧场害草。今年拜耳也将推出用于去除诸如水果,坚果和橄榄等特殊作物中阔叶杂草的Indaziflam,据称它通过抑制纤维素合来除去害草。
新技术对研发的帮助也尚未可知。虽然巴斯夫的Kixor中结构上侧链的革新是组合化学和计算机对特定类型分子模型优化相结合的成功范例,此外,基因组学和代谢组学在新害虫防控机制的研发中被寄予厚望,但是理论和实践往往是两码事,草类适应土壤和天气状况,并且赖以生长的生理技能并不能简单地用计算机模型予以模拟,那些顽固草害早已变得滴水不漏,很难找到攻击它们的弱点,因此需要将化学,生物学,农学的诸多经验结合起来才有希望战胜它们。
(未完待续……)
即将发表
下篇:
杀菌剂:传统抗病功能外搭上增产顺风车
AgroPages世界农化网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