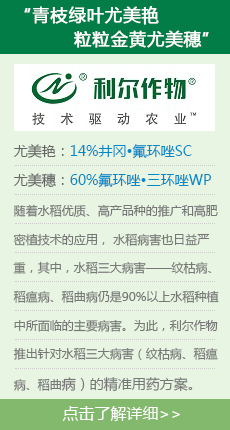无论是著名的农达还是其它的非专利除草剂,都抹却不了草甘膦最畅销除草剂的盛名,它可以用在包括包括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以及大多数中耕作物上,可以一扫而光地去除那些草类,但随着时间流逝,许多在它的威力下幸存的草类正在将它们顽强的生存能力传续给下一代,导致了草类抗性问题的产生。
自孟山都公司1996年首次推出了这个除草剂,随后不久又推出了具备相关抗性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以及其它转基因系列产品,使它们相互走向盛况。2010年,美国所耕种的大豆作物中有93%具备耐草甘膦性状,棉花占78%,玉米占73%,虽然其它的种子公司也出售耐草甘膦种子产品,但是孟山都却占据了大多数种子市场。
著名的对转基因作物持否定观点的组织——关切者科学家联盟UCS(Union of Concerned)一向认为转基因作物可持续农业毫无益处,但是在谈及草甘膦时,却一改往日的偏激“草甘膦是百年一遇的产品,没有任何产品能够替代它,它的确是个杰出的产品,我们正在挥霍它!”
它的好处显而易见:它是跨防控谱的产品,无论是阔叶草类还是牧草,其它的除草剂一般只对其中的部分有效;它能真正的斩草除根,可以放心的进行轮耕而不必担心没有斩尽杀绝,如有必要,还可再次使用;因为是非专利产品,价格便宜,更容易让农民青睐;它的毒性比其它产品更低,对农业人员来说更安全。
它如此地高效和使用方便,实在是宠坏了那些农民。种植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耕作系统实在是太简单和傻瓜式了,所需做的仅仅是购买种子和在田里喷洒而已,草甘膦会将作物之外的植物一扫而光,让许多农民变得懒惰了,一些农民们抱怨,以前一个好农民的象征是拥有一片无草的庄稼,而现在因为草甘膦,人人都能拥有一片干净的田地,对于所有的勤恳者和懒汉,都是毫无例外地得来毫不费功夫。
然而草类学家指出,日积月累,草类会对杀死它们的除草剂产生抗性,所以草甘膦抗性的问题的出现自然无法避免,现在它也的确在愈演愈烈,自十年前特拉华出现第一例耐草甘膦杂草——加拿大飞蓬以来,全世界共出现了21种对草甘膦产生抗性的杂草,其中美国出现了11个,好在它们只是局部出现,问题尚不严重。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草甘膦兴起同样与草类抗性有关。十年前,通过阻碍氨基酸合成的乙酰乳酶抑制剂类除草剂就是因为一些如苋菜藤子之类的草类产生了耐药性,而使得耐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得以流行,并且助推了草甘膦的兴起,但讽刺的是,这些杂草也开始对草甘膦以及其它种类除草剂产生了抗性,成为了名符其实的“超级杂草”。
包括孟山都自己的专家也承认,它们的转基因作物对草类抗性的产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草甘膦主要用于免耕操作,仅仅在播种前喷洒草甘膦即可,很多草甘膦用户虽没有采用免耕方法,并且播种的较早,好在杂草接触草甘膦的机会也尚且不多。
然而转基因作物的使用却大大增加了对草甘膦的依赖度。因为它可以单独使用并且在整季均可提供控草效果,它成了惟一一个能使用在大豆作物上的除草剂,除了作物,真可谓赶净杀绝,但是能在这“浩劫”中顽强生存下来的草类,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问题抗性杂草。
从历史上看,解决草类抗性的手段是采用不同机制的除草剂,因为新机制的除草剂能找到草类的其它弱点,并予以消灭。种植户也相信,一切问题都有办法解决,总会有农药商来研究新产品来对付它们。一些农药商也的确在不断推出新产品。
但窘困的是,二十年以来,没有任何新的除草机制被发现,也未知任何农药商在进行相关除草剂的开发。
相关新抗性转基因作物的研发状况也同样不容乐观,一些公司采用不同抗性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抗性问题,这又使得一些老旧产品如2,4-D,麦草畏等重新焕发生命,然而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倒退,因为这些产品往往高毒高风险的。
此外,这些耐草甘膦的草害往往难以用其它的除草剂清理,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在这场战争中,草类将获得胜利,我们在和草类的争斗中,的确因为有了领先的技术而足够幸运,但是在过去的四五十年中,玉米-大豆的轮耕种植体系的统治已经完全可以选择出草类中的佼佼者,它们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来适应这种耕作体系和我们所用的除草剂了。
始作俑者孟山都也不得不一面承认抗性问题的存在,一面向用户保证情况尚在控制中。但所能做的也仅是它了解客户的担忧,也在为解决这些问题和用户,科学家,以及公众机构合作来控制这些问题。
对于农民来说,这些方法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回到草甘膦之前的日子,得走到田间地头,观察何处,何时,何地产生了何种杂草,之后为它们选择特效的除草剂,在播种前,必须确保田地已经“干净无草”,还得考虑轮种哪种作物以及适用于何种除草剂。
改变这些的确很难,因为我们早已把农业当成工业看待,将种植视作工厂式的生产般处理而忽视了生物多样性,一味地为了追求高利润在每一片土地用同一种方式千篇一律地处理农田,却不肯花一点时间来个性化地对待任何一片土地,因此导致我们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
AgroPages世界农化网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版权!